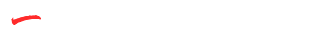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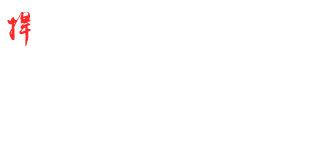
07.23
2024
07.05
2024
07.02
2024

宜宾市农业科学院始建于1958年,是从事农作物育种、农业生产技术、农业机械与装备研究的综合性市政府直属公益一类农业科研单位,现有在职职工144人,其中专业技术人员120人,高级职称50余人,具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、省学术技术带头人、市级拔尖人才等6人次。
现有水稻、玉米、高粱、油料、蚕桑和食用菌、农业装备、花生和烟草、果蔬花卉、畜牧水产、特种作物、农业资源和环境共11个研究方向。常年承担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、育种攻关、科技成果转化等各级科研项目,拥有国家、省、市科研平台18个。
率先育成四川省首个浓香型优质三系不育系宜香1A,其品质和产量配合力协同改良研究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,累计组配水稻新品种110余个。截止2022年底,累计育成农作物新品种204个(次),研制推广适宜丘陵山区作业的现代农机具10余个;品种权授权49个;国家专利135项。获得部省市科技奖180余项,其中农业部“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”一等奖2项、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3项、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4项。先后两次获得农业部“全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”先进集体、“四川省农业丰收奖”先进集体、全省农业科技创新先进集体荣誉称号。
06.16
2024
06.16
2024
26
2024.06
19
2024.06
14
2024.06
12
2024.06
31
2024.05
29
2024.05